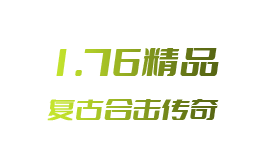
枫桥遗响
一少年时常翻读唐诗,于瓜架下或柳荫里,那时去过的地方不多,却从诗句里觅到了许多水意氤氲的处所:斜阳衰草的洛阳、霁色林表的终南、十里春风的淮扬,还有月落乌啼的枫桥。这些地方,似乎都在历史河流的彼岸,是可
一少年时常翻读唐诗,于瓜架下或柳荫里,那时去过的地方不多,却从诗句里觅到了许多水意氤氲的处所:斜阳衰草的洛阳、霁色林表的终南、十里春风的淮扬,还有月落乌啼的枫桥。这些地方,似乎都在历史河流的彼岸,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
对于枫桥,我常常抱着这样的遥想:秋风抚起的时候,独自乘一叶苇舟,沿着凝碧古朴的运河划行,薄暮时分停泊在那座烟水迷蒙的枫桥边,听听船底流水声和骤起的钟鸣,看那隐约的桥影苔痕、起伏的蔓草波纹呼应江枫渔火,一定能洗濯瞬间的烦嚣、承接千年的清愁。
当然,这些只是纸上的遐思,真实的风景永远在脚下。去年夏天,一行人从上海看世博回来路经苏州,都说要看看唐诗里的枫桥,用不了太多商量也就去了。
到枫桥景区的时候正是晌午,阳光强烈有如射线,投落在这一爿园林、一派水上,它散发的热度煮开了一锅沸沸扬扬的蝉鸣。黛色瓦片、粉色院墙、绿色杨柳和红色宫灯,阳光的曝晒下全无精神。方方的亭榭、长长的回廊、弯弯的枫桥,到处布满熙熙的人流、嘈嘈的人声。从枫桥上来回走了两三遍,我找不到半点诗歌里的感觉。
看不到一株枫树和一朵渔火,听不到一串橹响或者年青吴娘的湿润歌声,当然更听不到那在半夜才响起的寺院钟声。这还是枫桥么,那长在历史的甬道上的苔痕呢?那飘远了诗歌风流的河水呢?那托举了诗人哀愁的孤舟呢?那明灭在浩阔江面的渔火呢?一并雨打风吹去。远远望去,在枫桥的身旁,新修的河道里,数只机动船“突突突”地掷水而去,很是决绝。
烂璨的阳光,能让法国印象派先驱马奈找到景物准确的色彩,却不能让我找到对那首诗歌的准确感受。我需要深入一个诗歌的假象夜晚,让一朵明灭的渔火或者一滴残留的钟声呼应我的心情。
二
在遭遇张继之前,枫桥只是一座江南常见的单孔石拱桥。大运河在此通过,这里又是官道所在,南北舟车在此交会,便成了锁钥之地、羁客理想的休憩之所。隋唐时每到夜里航道就要封锁起来,因此这座桥也就被当地人称作“封桥”。然而,当它遇到张继,连名字也被更改,变得更具诗意了,也更有名声了,引得了明代高启的惊叹: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
千余年前,诗人张继参加京试不幸落第,于是从长安辗转经过运河一路南下,经受了闱试失败的巨大打击,诗人的心一定是沉痛的,面对眼前烟波浩渺的河水,他一定想到许多许多,想到攻读诗书时的古井静水,想到考前立誓的豪情潮涌,想到人生路途的云诡波谲,如今都付之东流了。以致于他经过枫桥时,拒绝船夫的邀请,不愿上岸去看看古镇的繁华之景,宁可独自呆在昏黄夜色中,蜷缩在一卷硬冷的被衾里早早睡去。
是生命的内觉,还是骤然在耳畔响起的乌啼和钟声,让诗人从脆薄的梦境中醒来。他看到,斜月已然西沉,夜空白如清霜,水面上一派沉寂,只有流水轻轻抛托船身。江岸枫树、江上渔火,清旷的苍穹下皆可看见,乌鸦在唤叫,寒山寺送来了钟声,虽被空间稀滤,但明显能感觉每一击钟声颤动的音晕。一时间,诗人突然感觉到一种更为阔大的愁绪充盈在天地之间,似乎把个人的愁闷冲刷得一干二净。此刻,在他看来,生命的内空其实远远大于拥挤的世界。几乎是情不能已,他挥笔在几案的纸页上写道: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的偶感,竟成为大历诗歌中的压轴之作。这,仅仅是偶然吗?
至于“夜半钟声”,欧阳修在《六一诗话》里曾提出了质疑:寒山寺距离枫桥有三十里之遥,哪能隔空传如此之远?是耶非耶已不重要,我们从纸页间竟找出了这位北宋文豪“嫉妒”两字划过的痕迹。
三
在张继的眼中,枫桥是寂寞的,这是“一座小小寂寞的城”(台湾诗人郑愁予语),然而,在他之后,枫桥又是热闹的。有关枫桥的诗作不胜枚举。
晚唐诗人杜牧大概开了一个好头,他在《怀吴中冯秀才》中写道:长洲苑外草萧萧,却忆重游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北宋孙觌写过《过枫桥寺》,他来枫桥的时候已是暮年:白首重来一梦中,青山不改旧时容;乌啼月落桥边寺,欹枕犹闻半夜钟。南宋诗人俞桂倒是挺怀念年青时在枫桥边夜宿的情景,他在《枫桥诗中》写道:昔年曾到枫桥宿,石岸旁边系小船。同时代的大诗人陆游,骑驴赴蜀正值夏月,经过枫桥已是重游了: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他的好友范成大来时却在春季:朱门白碧枕湾流,桃李无言满屋头;墙上浮图路旁堠,送人南北管离愁。明代诗人高启在《将赴金陵始出阊门夜泊》中写道:正是思家起头夜,远钟孤棹宿枫桥。清代的王渔洋泊舟枫桥,诗兴难抑于是写诗两首寄给了他的兄弟,其中一首最为人所推崇,他写道:日暮东塘正落潮,孤蓬泊处雨潇潇;疏钟野火寒山寺,记过吴枫第几桥。以枫桥为题材的诗作,如同漫山的枫叶,太多太多,而诗作中无一例外的愁绪也如枫叶,点点离人泪。
一场有关枫桥的诗歌接力赛就从张继手中开始延伸,整个过程又像马拉松,因为它的时间跨度竟然长达千年。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那么多的诗人是怀着怎样的心理,总想着如何“重复昨天的故事”,但无论怎样的努力,他们的诗作都无法突出重围,无法跨越《枫桥夜泊》的意境,像给他们念上一道魔咒,无法摆脱。
张继,这个落魄的诗人,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凄美的结,这是情感之结,也是诗歌之劫。
于是,在后人眼中,枫桥永远被愁云恼雾所笼罩。
四
其实,当时枫桥的情形绝非如诗作里那样凄凉。大运河的开凿,让枫桥这样的锁钥之地迅速崛起。张继到来的时候,枫桥已是繁华之地,舟车汇集、茶米散香、酒旗招展、人来人往,这种情景延续或有七、八百年,直到明末清初,苏州还流传一首俗谚:“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由此可见枫桥古镇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但是,在张继的心中,集镇的繁华似乎于己无关,他甚至忽略了身下这条凝重的河水(唐时水面之阔,张继把它写成江水了),只关注了水面上飘渺的钟声。可能受他的影响,千年以后,戴望舒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60年代农家“富裕”轶事
下一篇:袅袅不绝的美丽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