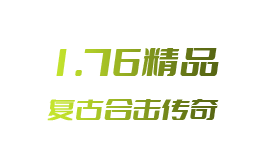
读《激荡中国海》
【1】沉重的好书最近在读一本好书,但却读得很慢。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纪实文学《激荡中国海: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作者王佩云)最近两周一直被我带在身边,往往是读一段想一会儿,边读边想,边想边郁闷,
【1】沉重的好书最近在读一本好书,但却读得很慢。
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纪实文学《激荡中国海:最后的海洋与迟到的觉醒》(作者王佩云)最近两周一直被我带在身边,往往是读一段想一会儿,边读边想,边想边郁闷,又时时夹杂百爪挠心、烦躁莫名的复杂体验。就这样,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用了两周的时间才得以读完。阅读速度如此之慢并不是这本书不吸引我,而是因为它实在太沉。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纵古论今视角,它上溯600年,以历史时空为纵坐标,以海洋为横坐标,锁定那些与民族荣辱和国运兴衰密切相关的海洋意识、海洋国策,层层剖析自明朱元璋以来一个个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梳理600年来国人在海洋、海权、海防等方面的决策得失,分析这些得失背后的主客观原因,以史为鉴,直面现实,以忧患于华夏子孙后代未来生存空间、生存资源的使命感,探寻当下中国在海洋战略安全、海洋主权保卫、海洋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大命题。
王佩云先生曾是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队伍中的一员,亲历了海洋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中有令人振奋的消息,比如四海对外开放;也有令人忧虑的消息,比如国家在南沙海域的油气资源被周边一些国家肆意掠夺,而国家在东海及南沙进行的勘探开发活动,包括合作和自营,却受到某些国家的无理阻挠。海洋形势的严峻令他深深不安。多年前,他与《中国海洋石油报》的同仁率先提出“蓝色国土”概念,通过各种方式在国人中进行普及宣传,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报社总编工作岗位上退休后,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积极关注、跟踪和思考海洋问题,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以一届平民知识分子的睿智眼光和卓越的思维穿透力,著成此书。他在《激荡中国海》前言中说:数百年来的痛苦实践告诉国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复兴,强国必须强海。而强海是一个涵盖非常广的庞大系统工程,不是说强一下子就强得起来的。最根本的,要唤起全民族的海洋意识,起码要让国人有国家、民族“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的警醒。
阅读这本书——说实在话,并不是一种享受,不是美妙的冲浪和轻松的漫游——是一次沉重的跋涉,是五味杂陈、苦酸涩咸的复杂感受,很多时候甚至是一种折磨,它令人体验到汨罗江畔屈原大夫的“天问”情怀,它让人无数次的发问:为什么?为什么!
【2】忧患意识
最近在凤凰网专栏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人只有死到临头时才会想到团结!再以巨大的损失取得惨痛的胜利!说白了就是缺乏忧患意识!”
这位网友的情绪大概与鲁迅先生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如出一辙。一个人,如果未曾在一件事上注入深厚感情,自然也不会患得患失,更不会生出哀怨。这种情愫,也与我在读《激荡中国海》时曾经衍生出的某种心情,有了些许呼应。
阅读时,我脑中经常盘旋着《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句话中的几个词组忽然引起我的注意,比如“最危险的时候”,比如“被迫着”,又比如“最后的吼声”。最危险,最后,被迫。这都是些什么样的词汇啊,顶尖级的最极端的情形,不外如此,难道你还能找到更高级别的形容词?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在那个国破家亡,大片国土已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最危险的时候”,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们“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确,屠刀已架在了颈项,退无可退,此时再不怒吼,更待何时!抗战初期诗人田间创作了一首著名的诗: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经过8年抗战和3年内战之后,自二十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人享有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光荏苒,弹指60年。尤其是通过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国家富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然而从富有到强大,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海防、治海能力、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迫切需要引起重视。
如今我们唱着75年前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和真正要义,为了避免全民族再一次上演“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不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像凤凰网那位网友所谴责亦即所渴望的那样:中国人,你再也不能在死到临头时才会想到团结!再也不能以巨大的损失取得惨痛的胜利!再也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3】如何才能变成“白痴般部落”?
《激荡中国海》开篇第一章是由明朝开始的。
1371年,朱元璋颁布禁海诏令,此后,每隔两三年颁一次诏,为保证落实到位,每出一诏,立即派遣身边重臣沿海巡视,查办违令者。为避免一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干脆将下海捕鱼也列入禁止范围。如此禁来禁去,最终禁到造船这个根本上,终至“片板不许入海”。
王佩云先生慨叹:这些现在看来实在有些冒傻气的行为,如果仅朱元璋本人一时性起也就罢了。不幸的是,他以开国之君的威权,将其写进“祖训”,提升为既定国策,并且纳入“大明律”,使之制度化和法律化。严厉告诫子孙:“有违祖制者一律以奸臣论处”。由此,海禁一直贯穿于大明朝200余年的历史长河,朱元璋过世之后的15个朱姓皇帝,一个个只有时松时紧的区别,却无一人敢说半个“不”字。其中,如朱棣这般具有雄图大略的继位者,纵有废止海禁之心,亦无违抗祖制之胆。
中国,本来由郑和及一些前辈率先扬起了寻找世界的风帆,忽然沉睡下来,等待西方世界来寻找。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同样谈论到摧折大明朝远航风帆的“禁海令”:
中国一直是陆权国家,海岸线虽长,却不重要,原因之一是陆上有够多的空间可以发展。七世纪以降,唐宋王朝才有繁盛的海上交通。蒙古帝国时,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