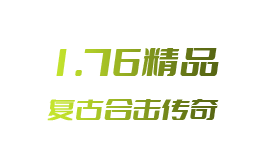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会往哪里去
近来,以万分虔诚之心如饥似渴地,像读《圣经》一样在刻苦研读由青年学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所合著的高等教育文科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认真研读之后,受益匪浅,感慨良多。连同先前已经
近来,以万分虔诚之心如饥似渴地,像读《圣经》一样在刻苦研读由青年学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所合著的高等教育文科教科书《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认真研读之后,受益匪浅,感慨良多。连同先前已经读过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编》(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郑万鹏著),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轮廓和脉络在脑中大概有了一个印象,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千回百转的路!如今,中国文学在经历了太多的反反复复之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回她会走向何方呢?她要走到哪里去呢?――这回就让我这个杞人忧一回天!这还要从文学与政治、与社会、与革命、与人、与诸多外部事务的联系以及文学内外部的争论说起。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三编第三个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三节《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中说,“40年代由于战争带来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文艺思潮也随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文学论争比以往更为频繁和激烈。”在第二个争论“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中他写道:
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敏感的理论问题,又常常引申为政治问题,在40年代曾屡次引起论争与批判运动。比较突出的就有两次。第一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初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等人的政治性批判。在“整风”之前,延安文艺界曾经出现过一股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潮,其特点是强调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重视文学的特殊功能,强调更有力地发挥文学认识生活和批判现实的积极作用。当时担任中共宣传领导职务的周扬,通常发表文章都是从文学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方面立论的,较少谈文学的内部规律。但他在1941年7月发表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却主张延安应有“创作自由”,欢迎作家的批评,“努力祛除那引起人们苦闷的原因”,这篇文章实事求是,结合延安实际,是对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实事求是精神的一种阐释,在当时发生了重大影响。随后,丁玲、王实味、罗烽、艾青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主张文学的真实性与独立性,强调以文学为武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丁玲先是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后又陆续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揭露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与缺点,主张发扬鲁迅“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精神,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罗烽在他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也认为“光明的边区”也存在“黑白莫辨的云雾”和“脓疮”,因此,作家有责任用杂文的武器来清除现实中陈腐的思想行为。艾青则发表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从文学的特殊的社会功用角度,指出了作家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或“百灵鸟”,而是“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因此,他要求领导者“了解文艺”,“尊重作家”,“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使文艺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到推进作用。紧接着,王实味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引起更大反响。王实味在文章中论述了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的社会职能和两者的关系,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他提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呼吁艺术家们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担负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应当“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1941年到1942年初在延安发表的上述杂文、小说,其所主张和体现的文学理论倾向,汇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潮流,其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等诸多命题的讨论,既坚持了革命的追求,又重视发挥文学的独特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眼光。可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极其政治化的环境中,这些有意义的探讨被看作是出格的异端邪说,文艺问题的论争很快被政治斗争所粗暴地取替。王实味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清算,戴上了“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特务”、“探子”和“反党集团成员”等莫须有的罪名与帽子,受到不容置辩的严酷的批判,后来又随意地被处决。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人的上述讨论文章也长期被视为毒草,一再受到政治审判式的批判。
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在国统区重庆也发生过一次。1945年11月,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在重庆上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周恩来领导下,《新华日报》组织了对这两个剧本的讨论。《清明前后》的题材与主题都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义,但艺术上有明显的欠缺,而《芳草天涯》则艺术上颇有特色,但与现实政治有一定距离。在座谈会上有人因此发言,认为存在着“有害的非政治的倾向”,说“有一些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并有马克思主义“此调不弹久矣”的说法。这样的观点,自然引出了不同的看法。时为中国青年艺术剧社演员的王戎首先著文,批评《清明前后》,并将大后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倾向产生原因归于“唯政治倾向”,显然针对着前述有关“非政治倾向”的批评。后来何其芳又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邵荃麟发表了《略论文艺的政治倾向》等文,批评了王戎等人的观点,力图从政治性艺术性的统一上去说明问题,基本上坚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在讨论中,冯雪峰曾以“画室”的笔名发表《题外的话》一文,只是反对将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割裂开来,强调“对于作品不仅不要将它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分开,并且更不能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冯文实际上是对《讲话》的有关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何其芳在《关于现实主义》中也就根据《讲话》的观点对冯文提出了驳难。但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冯雪峰的不同意见却被当作了“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罪证”。
第三个论争是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
当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国统区后,引起文艺界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