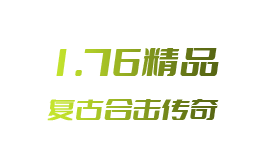
从苏联模式谈起
普湾新区于当下建设,那是我未来的大学。此刻我想和我的大学谈谈。当然我不是校长,只是一名大一新生,但这不妨碍我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高度上去打量它。首先我想说伽利略低头认错,承认地球不转;拉瓦锡上断头台;茨
普湾新区于当下建设,那是我未来的大学。此刻我想和我的大学谈谈。当然我不是校长,只是一名大一新生,但这不妨碍我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高度上去打量它。首先我想说伽利略低头认错,承认地球不转;拉瓦锡上断头台;茨威格服毒自杀;老舍跳太平湖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不可避免于“当下”留下了它们的影子。我把手贴在“当下”,度量这片土地的组分,揣测着这方寸土壤于大环境下又能孕育些什么?我觉得一个人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比重要的,大学亦是如此。既然要定位,就一定要把自我放到一个坐标系中。有了参考和比较,才能有一个自我定位。世界上,有培养将军的学校,也不乏培养士兵、排长、连长的学校。前者更趋向于一流大学,后者更接近于社区学院的概念。这里,不得不提下苏联模式和美国教育。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换四、五个工作,他们倡导的是一种通才教育——allrounder,就是培养一个通才,一个全才的人才。至于苏联教育模式,中国从建国初期到现在一直沿用的教育模式——强调专业性。(专业性学校培养专才,学校就培养一些针对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学生。)我个人认为,在建国初期,人才短缺的情况下,强调专业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当时的确有它的好处,学了马上就可以用,不过也不可避免的带了功利色彩。但我始终认为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通学教育必将成为主导。顺便补一句,专业性很强的院校,如果只囿于自己的行业,就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有人读了还不甚明白。我愿意更详尽地阐述下。本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苏两超级大国争霸,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当时苏联的工程师是美国的好几倍,但结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想过。前苏联搞的是专才教育,当时兴起大量钢铁学院、纺织学院、地质学。在崛起的时代里可以是这样的,当时钢铁的确是国家经济的命脉。但经济发展是千变万化的,总有一天钢铁行业不需要这么多的人才,总有一天,纺织学院压根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我试问先前那么多涌入此类行业的人才该去哪里找寻饭碗?这个问题的提出必将摆到台面上,在国家转型期这一阶段里,必将引起动荡。所以未来的中国的教学制度必将是通才模式——“通”是指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才”是指加上某种特长。
拿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话来说“我国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苏联模式有其价值,但若把阶段性的东西当成制度性的东西那就错了。一切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作出调整。”我觉得他概括得很好。他的观点我一点都不反对。
与之相佐的观点还有“社会形态决定高等教育的定位。”一个不发达的农业,一个欠发达的工业,一个高新技术比较发达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念叨这么久的社会形态,是时候该换换形容词了。你说,通才教育的道路还会远吗?
仰望完星空,视角一转,立足当下。
中央财大的校长王柯敬曾说过“缺乏人文底蕴和基础知识,年轻人就会缺乏后劲,大学也将随之成为职业训练场。现实的状况是谁都有功利心,体现在学生选择课程上就是更关心对就业的影响。”在他看来,那是发端于体制的一个矛盾。
谈到体制,我想到大学校长”谱系”和教师评价体系.对这我只阐述,不做过多评述。
校长“谱系”分三类:一,前辈教育家和学者.二,党的高级干部,大多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三,政工干部。
记得曾与浙大校长潘云鹤交谈,他的形象完全契合千百年来国人对学者的一般期待:国字脸庞、伟岸的精神世界、严谨又不失亲和力.他的“可爱”或者“魅力”更多体现在细微处,诸如他会说“校长要参与科研教研,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官僚。”诸如,他会说“校长不仅是职务,更是偶像。对于他的观点,我大抵是认同的。或许这也折射出我对一校之长的些许期盼。
至于上文涉及的教师评价体系,相信大多教师都是无奈的。在国内,作为教师,通常必须考虑每年能够发表多少论文,出多少成果,否则评价教授的硬指标就不够。这种现状难免会影响到教师授课的精力和水平。我认为,作为教师的评价体系,必须同时以承担教学任务为指标,要做教授必须授课。
分析丈量完“当下”这片土壤后,我想谈谈我的大学。如果你想建一个世界一流的豪华别墅,从第一块砖开始,你就要按照豪华别墅的要求去做,办一流大学也是一样,从招第一个人起,就要按照一流大学的标准去招。如果先招三四流的教师,在他们的基础上再招一流人才,那样很难。总之起点一定要高。这里提到“一流大学”,其实也是一个“谱”,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我们要尽力向这个群体靠拢,哪怕无法跻身,但心一定要向着那里生发。
其实大学的风格与它形成的文化积淀直接相关。而这风格又能反见之于其学子。“一个复旦大学和一个上海交大的学生同样走在路上,你能很快分辨出哪个是复旦的,哪个是交大的。”说的就是这个理。
说到文化积淀,水产学院59年为海洋大学筑基,历史可称悠久,积淀可算广博。这得天独厚的优势,若不延续为文化软实力的母本,而是另起炉灶,那未免太可惜了。况且进入21世纪,没有必要“想吃猪肉,必须从养猪开始”。文化软实力的营造更注重自我有意识的运营,故美国人的历史自豪感也就不难理解。补一句美国的历史之于华夏盖只能取一瓢饮。
至于学术风格,不得不提北大所倡扬的“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比之更为尖锐的话语有“我尊重你,因为你是我的老师,但是否尊重你的思想是我的自由。”这话是我说的。你可能会觉得我很偏激,只是我清楚的看见学子之于大学,如大学之于城市和社会等同重要。
对于大学生,我想说老师对学生有怎样的取向,学生就会有怎样的价值观;老师对哪类人的偏爱,会很直观的影响大批量的学生——“偏爱”就是老师的价值观的体现。复旦校长王生洪说他喜欢有好奇心,有种执着的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学生。我觉得他这个对学生的取向就很好。先前我常思索我为什么活着?一直找不到答案。通过阅读书籍,我看到罗素先生交了一份很漂亮的答卷。他说“对爱情不可遏止的探究,对真理不可遏制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但我总觉得他的回答更趋向于“人为何而活”,而非“我为何而活”。其中些许微妙,只可揣摩,无
版权声明:本文由1.76精品复古合击传奇发布网原创或收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一篇:好人的命——写给……
下一篇:浅谈:爱情的感觉
相关文章
